假令,己生己世,盡業為所定者,汝將何如?
人生在世,種種抉擇,事無大小,實非汝之所選,皆係他人之所定者,汝將何如? 猶如富者自富,貧者自貧,善人衡善,惡人衡惡。
美、醜,強、弱,幸或不幸──而勝者、敗者。
若此儔者,皆自初始之際,業已定決……除此之外,無能為力者,汝將何如? 倘若萬事不決於己,命不可違者,汝將何如?
所言所行,實僅為隨波逐流者,汝將何如?
問矣,諸君以此為善乎? 有權殷富者,實非己力之所得,唯上天施予,莫過虛構玉座爾。汝,誠可滿足歟?
一無所有者,非因一片之罪咎,而遭此凌虐。汝,誠可許之歟? 否,無理如此者,豈能善之。 諸君飽受凌虐,為人踐踏,如今甚將遭害致死。吾一時之同胞矣。 諸君生為敗者,亦輒以敗者之姿死而復死。
汝若呪詛此一命運,則當皈諸吾之麾下。 爭戰百度,仍不得勝者,再戰千度可矣。
爭戰千度,仍不得勝者,再戰萬度可矣。
立下誓言,未來永劫,爭戰不斷,直至戰勝為止而可矣。 諸君若能履行如此者,則今諾許汝等,得為成就密術之部分。
奉為戰勝,望在永劫。
吾祝福之,兇獸之鬣──其絲絲毫毛,皆以諸君血肉編成。 諸君,汝將何如?
此時代之敗者矣。
令吾聽聞諸君之答言。 戰或不戰──?

- 【01】赤軍: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正式名稱勞働者・農民赤軍,略稱勞農赤軍。係西元1918至1946之間,隸屬俄羅斯蘇維埃聯邦之軍隊。於二戰後期,以解放歐洲之名,進行大規模之殺人、掠奪、強姦行為。按世界難民問題研究協會之統計,在進攻柏林時,遭赤軍強姦之女性數目高達一百九十萬人。二戰末期,蘇連撕毀日蘇中立條約,出兵千島列島、南樺太、滿州、朝鮮之時,亦鑄下為數不少之戰爭暴行。
- 【02】Panzerfaust:簡稱Pzf,直譯作
鐵甲拳 ,係一種以成形炸藥為彈頭之無後作力反坦克手雷發射器。其輕便易於攜帶,製造簡單而得以大量生產,更是世界上第一種拋棄式反裝甲武器。一般認為由蘇聯所研製之火箭推進榴彈 ,延襲了其設計理念。 - 【03】Schmeisser:Maschinenpistole 40,二戰時德意志國防軍所使用之短機關槍。Schmeisser為德軍對 MP40 之暱稱,源自著名槍械開發者 Hugo Schmeisser。然而,MP40實為 Heinrich Vollmer 所開發,唯不少槍械特徵類似 Hugo Schmeisser 所製,而造成此一誤解。
- 【04】Neumann 效應:Neumann effect, Egon Neumann 踏襲 Munroe effect 之研究,發現若炸藥上具錐形凹槽,得令一般情況下只可炸凹金屬板之炸藥量射穿金屬版,成為反裝甲兵器諸如穿甲彈之基礎理論。
- 【05】Mauser C96:由軍火公司
Mauser 所生產之自動手槍。一般略稱 Mauser 者,多半指 C96,或 M712。中文稱之毛瑟或盒子砲。 - 【06】第三帝國:Das Dritte Reich,未來帝國。納粹德意志以神聖羅馬帝國為第一帝國,普魯士王國主導之德意志帝國為第二帝國,自詡為
第三帝國 。此外,Reich 同時意味「未來」,希特勒亦計畫將柏林改名Germania ,作為千年帝國之世界首都。 - 【07】忠誠與名譽:納粹親衛隊座右銘:「
忠誠方是吾人之名譽 - 【08】
親衛隊 :Schutz-Staffel簡稱SS,原隸屬突擊隊之下,因長刃之夜事件協助肅清反黨份子而得勢,遂獨立門戶。配合培育優秀亞利安人之目的,入隊條件極為嚴苛,體能、身高、智商、家氏、血統、容貌皆在考選條件之內。然而隨親衛隊之範圍擴大,晚期新增部隊之考選條件則物未必如此嚴苛。相較於傳統德意志軍隊冷靜務實之特質,親衛隊不惜犧牲生命之性格令其大受希特勒所重用。聯軍為誇示戰功,亦有意無意地誇大其實力,戰場上諸多傳說更加深了親衛隊鬼怪般的形象。 - 【09】Dresden:座落於德國 Elbe 川谷間之都市。二戰時受到聯軍
無差別轟炸 而盡數化作灰燼。 - 【10】勝利萬歲:Sieg Heil。Heil 為德語中表示祝賀之語,同時具有健康、幸運、萬歲等意。Sieg 則意指勝利。一般認為,Paul Joseph Goebbels 於納粹集會中首次使用,其後廣為納粹所愛用。
- 【11】特別行動部隊:Einsatzgruppen,特別殺戮部隊、特別行動隊,又名突擊隊、別動隊、行刑隊。由 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 所成立之特別治安維持部隊,在占領地域進行便衣游擊隊之檢舉與處刑。由於其性質特殊,往往被解釋為虐殺專門部隊。而成員亦多半由治安警察骷髏部隊員與武裝親衛隊之犯罪者所構成。
- 【12】勾十字:卐、Hakenkreuz、Swastika。西方共通之幸運表徵,Swastika 一字本身即意味幸福、幸運。德意志考古學家 Johann Ludwig Heinrich Julius Schliemann 於特洛伊遺跡中發現卐字記號,並論證其為流傳於古代印歐語系之共通宗教記號。以故,納粹將之比定為亞利安人之象徵而在黨章、國旗等處廣為使用。
- 【13】Legion:古拉丁語作Legio,本特指羅馬軍團,其後泛指一切軍團。
- 【14】戰略級:一般而言,兵器可略分作戰術級與戰略級。戰術級蓋指一般戰鬥所使用之火器,戰略級則帶有特殊戰略目的,或可藉其成遂戰略目標者。諸如轟炸機、核彈等,皆為其代表。雖非絕對,在此不妨姑且將之視作頗壞力遠遠凌駕戰術級兵器之武器。
- 【15】魅力:Charisma。與Charming不同,意指一般人所無法擁有,得以魅了眾人之魔般魅力。語源為古希臘語χάρισμα,意味著寵愛、恩惠、贈禮。是宗教家、政治家、指導者所夢寐以求之特質。
- 【16】juggernaut:無法抗拒之絕對力量,壓倒性之破壞力。其語源來自
印度教 中毗濕奴 之第八化身黑天 之別名・世界之主 Jagannāth。 - 【17】黃金之獸:人稱 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 為
金髮野獸 。該字蓋源自尼采『道德之系譜』中,對強大無慈悲者之描述。  【18】避忌諱愛之光:Mephistpheles,於希臘語中意味著「不可愛上之光」。地獄大公之一,德國傳說中之著名惡魔,飛空魔神。形姿類似
【18】避忌諱愛之光:Mephistpheles,於希臘語中意味著「不可愛上之光」。地獄大公之一,德國傳說中之著名惡魔,飛空魔神。形姿類似獅鷲 ,亦似飛龍,據傳身上滿佈黑毛。時而幻化為老人或紳士之姿,面貌尖銳,帶山羊鬍,頭上生有一對小角,足則有驢蹄,背上則有類似蝙蝠之雙翼。熟稔天文學、占星術、氣象學,而兼知未然。擅長炎系魔法與幻術。擁有由兩隻龍所拖曳之馬車,有時自身亦幻化作長有雙羽之馬。充滿人類之淫欲,冥冥之中誘惑人為惡,逼迫人簽下惡魔之契約。在歌德 『Faust 』中登場而廣為世間所知。- 【19】言靈:寄宿於言語間之咒力。
- 【20】Viktoria:勝利女神之德語表記。Sieg Heil Viktoria 亦可譯作「女神,請將勝利賜諸吾等。」或「女神,請祝福吾人平安獲得勝利。」此外,Sieg Heil Viktoria 亦為 Herms Niel 所著之德意志軍歌・行進曲。
- 【21】Doktor Faustus:浮士德博士。Johann Georg Faust,十六世紀德國占星術師、鍊金術師。十六名獲
海德堡大學 授與神學博士號者之一,死於鍊金術實驗之爆炸而粉身碎骨。更因生前遭馬丁路德 批評其憑借惡魔之力等事,造就往後的浮士德博士傳說。『實傳浮士德博士』述說其欲以魔法陣召換撒旦,招來撒旦之從者 Mephistpheles,與之契約,出賣自身肉體、靈魂,使役 Mephistpheles。其後浮士德愛上附近的女子,卻因違反與 Mephistpheles 之契約而無法與之連理。與希臘神話之Helene 同居,並育有一子,最後為該子所殺。歌德以此傳說為原形,創作著名長篇戲曲『Faust 』。Faustus 為拉丁語,代表幸福、受祝福之意,德語寫作 Faust。 - 【22】大虐殺:希臘語 ὅλοςκαυστός 乃組合
盡數 、燒毀 二字而成,衍伸為拉丁語 holocaustum 後經法語傳入為英語。廣義指組織性大量虐殺。狹義則意指納粹德意志於佔領區劃內對猶太人之大量殺戮行為。 - 【23】永劫破壞:die Ewigkeit,聖槍十三騎士團黑圓桌十三位・副首領 Mercurius 為打破
永結回歸 而創之魔術體系。以聖遺物作為武裝,藉魂魄為驅式,令人獲得超人 之力的複合魔術。然而作為武裝、防具僅是永劫破壞所表徵之邊際效用之一,並非其全貌內涵。 - 【24】Carl:Carl Ernst Kraft,Karl Ernst Krafft之古語表記,效命於納粹德國之魔術師・占星術師。1939年,行文德意志
國家保安本部 ,預言並警告希特勒於同年11月7~10間將遭人狙擊。8日,果真於希特勒演說時發生爆炸事件。由於其預言過度精確,而被視作嫌犯,為 Reinhard 旗下之秘密警察局 逮捕,移送至柏林。Carl 利用此一機緣進入納粹宣傳省,為醉心 Nostradamus 之 Goebbels 宣傳相擔任情宣 事業。其於1940至1941年間,奉命針對德國未來解讀 Nostradamus 之預言。此外,據傳其藉占星術所卜定之吉日、兇日,對德軍之戰略規劃具有直接影響。其預言德意志宣傳省以及柏林將遭空襲而化作廢墟等事,亦一一中的。 - 【25】理想鄉:
時輪坦陀羅 中所述說之釋教理想鄉。梵语शम्भल 意味著用以「維持/準備/蒐集/養育」幸福者。 - 【26】聖櫃:
聖櫃 或稱約櫃,收納十戒石板之寶櫃,今藏於耶路撒冷神殿 。 - 【27】神怒之日:基督教之終末思想,預言世界末日之時,一切人類將於地上復活,接受審判。亦有以此為名之安魂曲,句首敘述:「震怒之日,即在於今。世界化作灰燼,歸於虛無。一如大衛與希維拉之預言。」譯作神怒之日、震怒之日、末世經等。
- 【28】超人:尼采之學說中,相對於凡人、
末人 ,在永劫回歸之無意義人生中,確保自我意識、善惡觀,不屈於世界之新人類。 - 【29】富士樹海:位於富士山西北之青木原樹海,林木茂密,極易迷路,加上「一旦踏入則無法走出」、「羅盤無效」甚至「飛機經過上空時,一切儀表失控。」等謠言,令其成為自殺聖地,吸引許多自殺志願者慕名而至。
- 【30】法衣:Cassock,一種聖職衣,為各宗基督教司祭所著。按慣例,修道士身著黑色法衣,其餘人等則身著青、灰或白色法衣。
- 【31】珠鍊十字架:天主教作
玫瑰經 祈禱時手持之道具。 - 【32】恐怖劇:原意指 Grand-Guignol 劇場而言,其後則衍生至該劇場所經常上演之類似劇種。語源雖源自以人偶劇知名之 Guignol,然而該劇場乃以演員為主之舞台劇。劇中角色常出現一般舞台劇鮮見之流浪者、街頭孤児、娼婦、殺人嗜好者等,又嗜以妖怪譚、忌妒殺人、殺嬰、分屍、火焙,傳染病,甚至為斷頭台斬首後仍能言語之首級等等為題材,故往往被歸為恐怖劇。時而使用血糊等特殊效果。又,其演出之成功與否,並非由觀劇人數,乃是由失神人數判斷。
- 【33】神意欲此:拉丁文 Deus lo vult,意為「此,
神 之所欲。」係十字軍 東征時所使用之聖戰標語,或譯作「替天行道。」 - 【34】那由多:梵語
नयुत 之音譯,或稱那由他,意為極大量數。一般係指1060,或有說為1072。
|
1945年,5月1日,德意志,柏林。 AM 0:27……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最終局面,化作空前絕後的總力戰。 不,或許該稱之為殲滅戰。 遭受壓倒性的物量差距所壓潰,柏林孤立無援,淪陷已在一步之遙。 五十萬 由悲鳴、槍聲、爆音所合奏的狂想曲非但未嘗間斷,更毫不容赦地響徹雲霄,彷彿欲將街道、人民連根拔除,毀壞、鏖殺個片甲不留。 鏖殺──男女老幼格殺勿論,不留嚼類。為了根絕世界公敵。 正義、復讎、愛、和平、壓制、解放、自由、平等──名份為何,其實無關緊要。 這狀況,毋寧是──只要握有出師有名的大義,人類說要有多殘忍就可以有多殘忍的最佳範例。如此事例,正在各處上演。 例如──在此。 在炫目的閃光後,爆音與爆炎隨之炸裂。 由於此次砲擊,數人──至少是仍具原形的屍體──有三名以上,被炸作微塵般的肉塊,散落街道之上。  「──狗娘養的!」
「──狗娘養的!」男子合著罵聲,手握 藉助後方 在扣下鈑機的同時,成形炸藥自Panzerfaust 前端射出。 砲彈以目所能及的初速奔馳,直至被吸入戰車側甲之中──著彈。 裝甲因 Neumann 效應[04]而溶解,戰車內部為超越數千度的火焰與液化金屬的奔流所肆虐。 男子投棄 Panzerfaust,改執 唯有殺、殺,不顧一切地殺! 不可保持清醒。 若不願戰死,則唯有嘶吼奮戰。 決計不可回首。 無止境地發狂作亂,令血液不斷升溫沸騰。 在震耳欲聾的槍火砲聲中,士兵們猶如祈禱般地復誦上述文句而相互殘殺。 當然,這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紛爭。縱使一時制住此處之戰鬥,對大局勝敗卻依然毫無些許影響。 德意志第三帝國[06]跌墬破滅的斜坡,獨裁者的夢想唯有在戰火中逝去。 餘留於此者,無非是與殘骸無異的敗者,以及彷彿禿鷹般貪食著腐肉的勝者。 無以逃脫之敗北。  抵抗不過是毫無意義的自我滿足,救贖不存在於任何角落。
抵抗不過是毫無意義的自我滿足,救贖不存在於任何角落。這已然跨越了絕望的深淵,恰似滑稽的鬧劇。 然而即便如此── 「殺──殺,再殺!」 這心臟仍在跳動。 這手上仍握著槍械。 仍有敵人,則非殺不可。 為何?因為這是義務。 什麼都好。只要有任何得以容許此一地獄存在之物,即便那是瘋狂,在此亦與祝福無異。 守備此街區的整個中隊,除了他們之外盡數全滅。這狀況已然無力回天。敵軍增援想必會在不久後逼至。 「還有 Panzerfaust 嗎?」 「您方才所用的,就是最後一枚了, 「我叫 Joachim Brauner。上士呢?」 「我是 Walter Görlitz。……唉,大家都不想和連名子都不知道的傢伙一起死吧。喂。」 Walter Görlitz 上士望向另一位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的年輕人。 「你叫什麼啊?」 「啊……那個……」 這個臉上難掩怯懦,視線徬徨遊走的年輕人,比 Joachim 更為年幼。 恐怕不過十來歲吧。如果 Walter 有孩子的話,約若就是這個年紀。 「我叫 Marco Schmitt,上士……」 「……是嗎。」 Walter 不會說出如:「對著這樣的小孩……」一類的話。因為說了也於事無補。敵人不會因為對方是小孩而高抬貴手。 原因無他,我等正是赤軍恨如蛇蠍的 Joachim 似乎已有這份覺悟了,但這位少年…… 「這戰爭結束後,柏林,德意志……會怎麼樣呢?」 「…………」 「我們的家人、朋友,此後究竟會……?」 「天曉得。這種事……」 「反正一定是那樣的吧。戰勝國擺出一付屌樣,裁斷我們是惡魔、非人道什麼的吧。真是笑死人了!」  在旁觀望不語的 Joachim 忽然一改態度地吐露苦水。
「我母親與妹妹都在 Dresden[09]。卻遭到轟炸,灰飛煙滅,連一小片殘骨都不剩。惡魔?開什麼玩笑!我們不過是為了祖國而戰罷了!而那些傢伙居然……可惡,小看我們!」
絕不投降。然而,就算捨命奮戰,也絕對無法改變勝敗已定的局面。自己沒有那般能耐。 在旁觀望不語的 Joachim 忽然一改態度地吐露苦水。
「我母親與妹妹都在 Dresden[09]。卻遭到轟炸,灰飛煙滅,連一小片殘骨都不剩。惡魔?開什麼玩笑!我們不過是為了祖國而戰罷了!而那些傢伙居然……可惡,小看我們!」
絕不投降。然而,就算捨命奮戰,也絕對無法改變勝敗已定的局面。自己沒有那般能耐。而就這樣敗戰的話,祖國將,子孫又將會…… 在名為戰爭的巨大波濤之中,無力的一兵一卒什麼都辦不到。 唯有憤懣、咒罵。面對 Joachim 的獨白,Marco 只能默然不語。 「所以我──」 「───!」 就在這瞬間,連續不斷的槍聲自側面傳來。 瞬間伏下身子的 Walter 與 Marco 勉強地逃過一劫,Joachim 則被第一槍轟爆了頭顱,接連而來的槍擊則將其身軀化作蜂窩。 「……畜生!」 在倒地為止的數秒之間,Joachim 的身體受機槍掃射而跳著奇妙的舞踊。 對於不久之前才立誓奮戰至死的年輕人而言,實在是過於唐突的終局。 這就是現實,這就是戰爭。沒有所謂的救贖、英雄,以及奇蹟,人命只能如臭蟲般默默消逝。 然而,如果對其抱有憤怒與絕望之念,自己亦將在轉瞬之間成為死亡之顎的禁臠吧。 不可思量任何分外之事。只有鞠躬盡瘁,履行自身的義務…… 「Schmitt!聽得見嗎,Schmitt!」 為了逃離彈幕,Walter 滾身躲入已開始頹倒之大樓的陰影中,全力嘶吼地呼喚僅存一人的名諱。 然而,得到的回應卻是──  「───!」
閃光、爆音、爆炎再度大作。
少年的上半身為砲擊所炸飛,滾落至 Walter 腳邊。 「───!」
閃光、爆音、爆炎再度大作。
少年的上半身為砲擊所炸飛,滾落至 Walter 腳邊。狹窄的道路瀰漫著鮮血與臟器的燒焦味。Walter 無力地跪在不斷擴展的血海之中。 「……啊啊,上士……」 「對不起……我派不上用場……」 大概撐不過一分鐘吧。光是在尚能言語這點就足以驚愕眾人的狀態下,少年強顏歡笑。Walter 不自覺地握住他的手掌。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如果死在這兒,那我們至今又是為何而戰呢……」 「上士,請告訴我。我們是惡魔嗎?柏林、德意志將會……」 「別說了,Schmitt……」 想當然爾,槍擊不會因此停歇。新來的戰車發出陣陣聲響而步步逼近。 Marco Schmitt 已然回天乏術。縱然是神,亦救不了他。 是以現在,身為軍人的 Walter 該執起的,不應是少年的手掌,而是殺敵的槍械。該豎耳傾聽的,不該是感傷的廢話,而是敵兵的吐息。 他明白。他比任何人都要明白,然而…… 「我們是做了什麼壞事嗎?所以才會遭到這種報應?我明白殺人的戰爭是不對的。但是,但是我們……」 Joachim 以及自己,至少大多數的士兵們,不過是為了守護祖國以及所愛之人,才執槍奮戰的啊…… 這,這真是如此罪孽之事嗎? 在邁向死亡的柏林之中,少年以斷斷續續的言語問著。同時,這亦無非是 Walter 想投諸上天的質疑。 「……恐怕」 然而,在不過數秒的鬱悶之末,Walter 短短地說道。 「錯不在戰爭,而是錯在敗戰吧。」 這是真理。是多麼殘酷而可憎的真理。 啊啊,所以啊,神吶──我對祢…… 「這樣的話……希望下次…能戰勝呢……」 Marco Schmitt 靜靜地在仰望蒼天的 Walter 腕中斷氣。雖為泥血沾污,臉上依舊浮出帶有稚氣的苦笑。 「……是啊,Schmitt、Brauner」 低聲自語的 Walter 臉上,也同樣浮出了苦笑。 「下次必要勝戰。下次不勝,則下下次。仍舊不成,便等下下下次……若可重複一百萬次,或許真能推翻此一終局。」  無聊,不過是死到臨頭者自暴自棄的誑言罷了……決非如此!
無聊,不過是死到臨頭者自暴自棄的誑言罷了……決非如此!Walter 替 Schmeisser 上膛,確認初彈裝填無誤,便一口氣舞出大樓的陰影。 「 自己接下來的命運,是如 Joachim 般變成蜂窩呢,抑或是如 Marco 般一分為二呢。 算了,是哪個都無所謂。 不過就是以天殺的死法,為這天殺的必敗之戰拉下終幕罷了。 捨身突擊的 Walter 腦中,只剩下這個想法。是以其自然無法預料接下來的展開。 Walter 頓悟到,理應無可能出現在市街戰等級的破壞力,方才就在眼前炸裂。  這,到底是……
這,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 街道……名副其實地,由自己捨命守護至今的此一街區,在瞬間化作一片焦土。 開什麼玩笑?雖然讓視覺與聽覺恢復正常機能著實花了不少時間,然而即便花了如此長久的時間,他仍然無法把握眼前的狀況。 能理解的,只有無論部下的遺體或敵方部隊,已然毫無所存的遭到轟飛罷了…… 即便遭受空爆,也不至於在須臾之間化作如此慘狀。Walter 自身雖未瞬間斃命,卻也不免身負重傷。 「……唔,咳」 被暴風轟飛的鋼筋和混凝土塊,不偏不倚地刺在自己的脇腹與背部。 一度緊握 Schmeisser 的右腕,自肘部以下早已消失無蹤,想來骨折、裂傷亦不在少數。 由吐血不止看來,有幾處內臟確實已被壓潰了。 致命傷。 「可惡……可惡,可惡!」 早已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怨恨什麼了,Walter 無我夢中地破口大罵。此時,那道聲音于耳邊再次響起。 美麗動聽的歌聲。 具有連大教會的聖歌隊,亦望塵莫及之「格調」。 然而任誰都能清楚地聽出,歌詠之人並非獻上哀悼,乃是投以嘲笑。 若可將之評作天使的歌聲,那時想必是在世界末日了。 寄宿於歌聲之中的,是對死者的嘲笑、侮蔑、凌辱,藉由蹂躪尊嚴而獲得悅樂的惡人性情。 那是遠遠凌駕一般常人所能抱持之惡意的,闇黑精神。
他是,理 應 早 在 三 年 前 就 已 死 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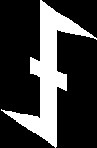 「Schreiber…… 不分敵我瘋狂肆虐,因而遭到肅清的白色惡魔。 為何會在此處…… 「唉啊,我才想是誰呢,看看這不是 Walter Görlitz 上士嗎?在 「嗯,不為什麼,我們都是軍人吧。戰鬥殺人不正是咱賴以為生的工作嗎?」 少年以如此輕佻的舉止環視四周,異變隨之而起。 如霧似靄,這一代漫起了不透明的陽炎。 同時,令人想掩住雙耳的呻吟聲令 Walter 震耳欲聾。 那是為怨嗟所糾纏,死後仍被詛咒受苦以至永劫的眾多死者之聲。 在那無數悲喚交錯的慟哭之中,先前為火焰所灼熱的氣溫,忽然激烈地下降。 這是眾多死者之魂魄嗎?在那幢幢陽炎中,Walter 似乎瞥見了 Marco 與 Joachim 之容顏。 以及,彼等所邁向的終途…… 溢塞空間的魂魄化作渦漩,為 Schreiber 眼帶上所鑲嵌之 吞噬著。這少年正吞噬著自己所殺之人的魂魄。 目睹如此乖離現實之光景,Walter 無法判斷此時應當憤怒或是悲泣。 若能在此失去理智,該會有多麼輕鬆。 「那麼,別了,軍曹。我現在是不走不行了,你怎麼打算?」 Schreiber 彷彿吃飽喝足,誇張地迴首四周,道出不明究理的話語。 所謂怎麼打算,究竟是指什麼。Walter Görlitz 已然氣若游絲,早非仍可行使軍人勾當的狀態。  「殺夠了嗎?」
「雖然就算現在再殺個幾千幾百名赤軍,也不可能有什麼改變就是了。不過,也沒有必要默不坑聲地束手就縛吧?看吶,這帝都柏林。簡直是慘不忍睹。這就是我等所追求之千年帝國的末日嗎?哈哈哈,怎麼可能有人服氣!」
服氣?你說服氣……
「辦不到吧?」
Walter 以好似要射殺這位少年的目光,嗔目怒視著面露獰笑的 Schreiber。 「殺夠了嗎?」
「雖然就算現在再殺個幾千幾百名赤軍,也不可能有什麼改變就是了。不過,也沒有必要默不坑聲地束手就縛吧?看吶,這帝都柏林。簡直是慘不忍睹。這就是我等所追求之千年帝國的末日嗎?哈哈哈,怎麼可能有人服氣!」
服氣?你說服氣……
「辦不到吧?」
Walter 以好似要射殺這位少年的目光,嗔目怒視著面露獰笑的 Schreiber。是啊,怎麼可能有人能接受這種結局! 有過朋友,有過家園,也有過所愛的女性。自己更是深愛這個國家。 這一切,終將因敗戰而蒙上污名。披上未來永劫,無所磨滅的污名。 這種事── 「無法原諒吧?讓那些低賤的劣徒自以為是地蹂躪帝都,強暴女子、濫殺孩童、吊死老人!」 「上士,忠勇的德意志軍人─Walter Görlitz 上士殿。讓我聽聞你的心意。你究竟,怎麼打算?」 「啊……呃……」 礙於汨汨溢出的血沫,發聲無法隨心所欲。然而心意已決。 誓言戰至最後的 Joachim,述說冀望反敗為勝的 Marco。他們的心意,以及自己的心意…… 眼前的少年無異是惡鬼之儔,卻已無關緊要。 自己,我想…… 「……想要戰勝!」 戰勝,為祖國獻上榮光。 為死去之夥伴與家族帶來安息。 亦為未來之子子孫孫賜與祝福。 更是,為己身之魂魄…… 「 
然而此時此刻,在 Walter 耳中卻是如此甜美,猶若天籟…… 啊啊,原來如此。這就是世界的終末嗎。 自今以後,己將加入滅世之軍勢。 構成魔獸之 Walter Görlitz 之魂,為嗜血狂醉之獨眼所吸入,消逝於虛無………… 同時,在別處,則上演著另一齣惡夢。 數十輛戰車編制之部隊,卻無法解決唯一的敵人。 ──不,其正因這唯一的敵人而邁向壞滅。 身處此異常事態之中心者,是一名漆黑壯漢。 在一絲不茍的軍裝之下,鍛鍊至極限的肉體,以鋼鐵形容之亦不為過。 猶如古代雕刻之藝術性,與狂暴武威之完美融合。 而其人,竟手無寸鐵。 赤手空拳。 其拳擊──光憑其拳力,就將戰車如紙糊般地貫通、破壞。 儼然超脫了人類的極限。 「──怪物!」 誠然,是即怪物。若非怪物,則是人形姿態之兵器,八尺身軀之要塞。無論如何,其必是超人之兵士,非人之怪物。  「開火──!」
若需補充,則尚餘一點。
「開火──!」
若需補充,則尚餘一點。這名壯漢,自先前開始,就 未 嘗 迴 避 任 何 攻 擊。 這身浴無數槍彈、砲彈,卻依舊毫髮無傷之肉體,儼然正是不滅。 然而,這亦是想當然爾。 為何如此?因為眾人咸皆知曉。 知悉這名男子,知悉其強大,知悉這位 應 當 死 於 一 年 前 的 英雄之名。 任誰都殺不了死人。 「──────」 男子口中洩漏吐息。 橫溢之氣息將四周瓦礫化作塵芥,更捲起熱風將之吹散。 撓曲至極限的肌肉,一如要尋求解放力量般地膨脹至極大。 其為鐵鎚。 世上莫有其無法粉碎之物,將一切強制終了之破滅一擊。 集束於拳上之能量令大氣產生熱差斷層,男子峻巖般的身軀在陽炎中晃動。 充實的氣體極度膨脹,其程度猶如要隨時脹破般,當下正是其即將破裂之瞬間──
遠遠超越了個人裝備乃至於戰車所能發揮之破壞限度。 毋庸置疑,這是如同將戰略級兵器[14]之威力──縱然不可能──任意集中於一點所造成的超熱量爆發。 足以改變地形之暴威留下痕跡,遍地化作火海。其中,則迴盪著不屬於現世之臨終悲嚎。 曝身於瞬間猛火之下,眾多士兵連影子都不剩地蒸發消逝──彼等冤魂發出怨喈之聲。  簡直與早先 Schreiber 所造成之現象一致。
「……無趣。」
「脆促,而且軟弱不堪。始終是低賤的劣徒之魂,令人倒盡胃口。」
幾經何時,一位鬱鬱謾罵之女子,佇立於漆黑男子之後。
簡直與早先 Schreiber 所造成之現象一致。
「……無趣。」
「脆促,而且軟弱不堪。始終是低賤的劣徒之魂,令人倒盡胃口。」
幾經何時,一位鬱鬱謾罵之女子,佇立於漆黑男子之後。若欲形容其樣貌,則是──紅蓮。 隨風盪漾的長髮,猶如鮮血,或是業火般的朱紅。 論其姿容,可謂美貌伶俐,然而覆蓋其左顏面的燒痕,則道出了美醜交織的悽慘。 「那麼,您是對我有何不滿呢,英雄?看你一副相當不悅的樣子。」 女子優雅地啣著雪茄吞雲吐霧,質問背後的男子。 毫無回應。 「……哼,也罷。配上濫殺過度的 Schreiber,正好能取得均衡吧。我不懂所謂武人之矜持,您就好好守著吧。」 「 畢竟,光依心情而將現在包圍柏林的五十萬赤軍鏖殺殆盡爾爾,不像是保有理智之人所會說出的話語。 「方才,總統閣下逝世了。」 「無論是夢想家的長官、或是喧囂的情宣人士,都將追隨其腳步而去吧。其後,這帝都將拖著大量市民與同胞的性命作陪,失守淪陷。──就犧牲而言,確實可稱作是嘗試創造聖櫃的適當觸媒。比起獻上幾百萬敵軍,應當守護之民、應當愛惜之友,爾等十人之命,遠重於百萬敵軍。這就是所謂人類。──你正因此道理而懊惱著吧?很好,苦惱亦將成為祭贄。」 「……Samiel」 至今默默無言的男子啟口。 「 「你……找那傢伙做什麼?」 「…………」 再度地,默不作聲。男子毫不回應。 女子訝異地瞇了雙眼,隨即發出無可奈何的嘆息。 「唉,又是一言不發。過於寡默的男子也是個問題。你該不會打算和那傢伙對戰吧。」 「此外,萬一果真如此,這可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只會徒勞無功,所以我勸你還是別幹了。那傢伙是絕對殺不死的。──不,就某方面而言,或許可以輕易的將之扭斷也說不定。」 「無論如何,那可是吾等的上司,更是首領的盟友。若你懷有叛意,老實說我也不能坐視不顧。」 「我無此打算。」  「我想也是。想來你那頑固的腦袋,豈會有此不軌之圖。是以我現在回覆你方才的問題。」 女子說著,以下顎一指,仰望虛空。 「我等黑圓桌指導者二人,親如兄弟。是以其身所在,必然已決。看吧。」 柏林之空,受鮮血與熾炎反照,染作一片火紅。 覆蓋帝都的戰火,其狀正映照於該處。 那是極其龐大,巨大異常的 在彷彿要貫串其中樞而屹立之尖塔上,或人正佇立其梢。 「全員傾注!此為吾等之主,偉哉破壞之君之御前。爾當噤口嘿默,括目拜聽其尊言!」 不知是何種方術之效,魔炮之聲猶若魔法,響徹柏林全市民耳間。 在此瞬間,兵士止住戰鬥,孩童止住哭泣,老人止住逃匿。 忘我。所有人皆陷入忘我之狀態,凝視空中的一點。 朱赤、鮮紅,為血與炎所映染之虛空。 化作魔女藥爐的柏林之 於千年帝國夢碎之日,輝耀的猛獸在此降臨。  髮如飄蕩之鬣毛,盡是金黃。
髮如飄蕩之鬣毛,盡是金黃。俯瞰世界,傲視一切的王者之瞳,亦是金黃。 遠較世上一切鮮豔而華麗,莊嚴、美麗的同時,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金黃。 不應存在於人世,不當愛戴之光之君王。 伴於其傍者,則是輪廓曖昧,剪影般的男子。 其外表看似老人,又似青年,更可看作任何事物。如隱士般毫不醒目,虛無飄渺。 對極般的兩人。而此二人,正是凌駕於一切瞻仰其姿容之者之,魔人中的魔人。怪物中的怪物。 「勝者自為勝者,敗者自為敗者。此皆與生俱來,無論欲步以如何經緯,終將歸至天命之末途──假令此世之理如此然,汝將何如?果真如斯,如何努力,如何怠惰,抑或祈求、懇願,其悉徒然。假令神之恩惠、制裁,莫過早已注定如此者……眾卿,被視作惡魔之子、世界公敵而慘遭誅滅者矣。汝等之身,實未帶一片罪咎,而因此故,竟為人所侵犯、掠奪、蹂躪、踐踏爾。身陷此一忌諱之 「欲逆天命──是邪?否邪?」 陰鬱之男聲,迴盪柏林,達至全市民耳際。 述說著,汝等將永恆受苦,無限遭害,永無寧日。 其聲猶若宣告最終判決之喇叭,帶著絕望般的說服力,沁入聽聞者之胸中。 擁有魔般 常人只消聽聞,必陷入混亂或為其所魅了。羸弱之人,則恐立地昏厥。 男子下令。  「思之者,戰矣!」
若欲改易此不遇之人生,則當獻上魂魄。
「若抗拒進入名為命運之
「思之者,戰矣!」
若欲改易此不遇之人生,則當獻上魂魄。
「若抗拒進入名為命運之黃金般的男子自遙遙高處,訴問匍伏地上之群眾。 「眾卿,所求者何?」 群眾之答覆,無須傾聽。 Doktor Faustus[21] 如是說:任誰觀之,皆為笑顏無異。同時,亦是任誰觀之,皆不似笑顏之異形獰笑。 ── 執槍者,將之置入口中。 執刃者,將之刺入胸中。 手無寸鐵者,飛身撲入火中。 開火、突刺、躍身,群眾紛紛自害。 百人、千人、萬人,群眾以異常之速度逝去。全數魂魄,絲毫不剩地為黃金男子所吸攝。 將帝都貪噬殆盡之 該人至今為止,業已吞噬數十數百萬之魂。 擎天之方陣,蓋可謂之為其最終階段乎。 將仰慕、崇敬自身,並對己尋求救贖之兵民獻上,以為生贄之祭壇。 此事何其悽慘、陰憺,恐怖而── 「……美麗。」 「簡直是悲劇……仰慕貴殿,貴殿應守護之眾人,因貴殿之故而逝去。貴殿將嘆息,喜悅,並將之化作己身之力歟。吾友──在吾人滑稽之一生中,唯一抱持敬畏之念的獸殿……貴殿自今而後,將成就何事?」 至今不言不語默默侍於身傍,剪影般的男子啟口質問。 「貴殿所求,究竟為何?」 「愚問。」 「法則之 「其事者何?」 「創造法則者。」 「原來如此,是即……」 神,抑或惡魔…… 剪影般的男子哼哼地震動咽喉,發出微笑。 「吾能得此優秀『學徒』,甚幸甚幸。現狀而言,得以正確理解 「Carl[24],當啟身乎?」 「是矣。不妨留置此名,捨諱離去。想來有朝一日,必得再度相逢。」 「半世紀後,東方之 「當然,寡人本意如此。Samiel、Schreiber、Berlichingen……吾欲率彼等而去。」 「善哉。此人選可謂無懈可擊。……毋寧說,除彼三之人外,無人足以伴隨現今之貴殿。」 彼等俯瞰眼下的地獄,同時以彷如對弈般之口吻交談。 評之親如兄弟,蓋無不宜。若論及此二人有何共通之處,勉強歸結,則當是其並抱持著超越常理之達觀性。 悲劇、喜劇,亦或任何事物,皆不值其發自內心感動。 雖說如此,亦非單純的冷笑家,更非感情麻痺,而是如同其存在持續磨耗……奇妙之「老態」。 而當下,仍有十人左右,仰首觀望此一光景。 彼等一皆身著軍裝,佇立在發出臨終悲鳴的柏林中,身上莫有絲毫損傷。 奉魔獸為君主之爪牙──在其之中,特別拔群強大者,是即前述三人。 紅蓮女子感極落淚。因身獲黃金指名之榮耀而奮起,於心中立誓將益深其忠誠。 白貌少年鬱鬱寡歡。悲歎暫時無法殺人奪命,心中盤算把握當下及時濫殺。 漆黑男子依舊無言。以陰暗的雙瞳注視剪影般的男子,除此之外不為一顧。 ”莫擔憂,汝願必叶。是以還請莫以如此可怖之眼神睨視在下。” 享受著伴隨如坐針氈之視線而至之壓力,剪影之男最後再度望向黃金男子。 「那麼, 「否,當誓令其成就。一昧傍觀,必無所成事。此誠卿之惡癖矣,Carl。」 「……確實。既此,不妨在此立誓何如?」 此日,以世界為敵,一再孤身奮戰之髑髏帝國步上壞滅之途。 無論真偽,科技力冠世當下之此國,暗地施行超越常軌之魔術儀式等事,亦是著名之逸話。 為神所選之 其人其物,究竟今在何處?抑或,其是否曾經真正存在,至今依舊朦朧不明。  ──現在。
2006年11月29日──富士,青木原樹海[29]。
──現在。
2006年11月29日──富士,青木原樹海[29]。AM 3:27… 四下皆為紅蓮之焰所環繞。 熱氣奔流自無名洞窟中突如噴發,鏟倒周圍數十公里之林木,並使之化作燎原。 此為氣穴。世界中猶如網絡般縱橫交錯之地脈與地脈間之交匯處。 一位男子自穴中步出。 由身著 然而,此時此刻,於此一場所,與烈炎一同出現者,果真可謂為聖之存在嗎? 相對的── 跪於男子足元,行臣下之禮者,則是一位黑髮少女。 察其膚色、容顏,少女必是此國之人。 少女面不改色地吐露出恭敬的言語。 「恕我無禮,聖餐杯猊下。Valeria Trifa 代理首領。將您請至此處者,乃係我個人之意向。需要自我介紹嗎?」 「不──」 「Leonhard,我還記得妳。當年繼承 Kircheisen 之位時,還是個孩子……妳變得更為美麗、強韌了。」 「惶恐至極。」 在四周,回蕩著有若悲鳴、叫喚般令人不悅的聲響。 這蓋是沉澱於此的自殺者之靈。對於糾繞而來之亡靈,少女不屑一顧。相反地,神父則慈悲為懷般地將之吸入、咀嚼。 此是醜惡而冒瀆之光景。  正如六十一年前的柏林。這莫非是其延續。 讚頌般述語之神父,及恭敬慎言之少女。 彼等相交三言兩語,內容卻不那麼重要。 諸如,神父乘著地脈自地球背面前來之事,以及少女曲撓其經路,將之導至此地之事。 對此無禮之謝罪,以及釋明此舉之正當性與必要性。 至於為何神父不可前往『彼處』之說明,則非在此所當言語之事。 要事唯有一件。 「那麼,從今而後──一同開啟爭戰之延續吧。」 如此而已。 彼等正將披露其長久以來等待、籌備,蘊釀多年之駭俗節目。 來矣,揭其序幕。 劇種為 弒殺、戮殺、殘殺,鏖殺殆盡。 掠奪、侵犯,並將之獻作生贄。 將勝利收諸吾掌。 納勝利為吾物。 何故── 「 無論百萬回,或百億回,必將爭戰不止,直至 既已誓言如此,則除此之外,別無他道。 神父對吟詠著 今宵,滅世 此事,世上任何一人,尚仍無以知悉…… 正田崇 『Dies irae 序章』 完  |
【wiederkehren】 (C) Light dies ira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2006~2010
当ページはlightより画像素材等の使用許可を得ています。
本頁所使用之畫像素材之類,既經light同意。切勿無斷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