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喜歡「勇氣」這個字眼,但是並不會喜歡所謂的「竭盡所有勇氣」的表現。
我喜歡「勇氣」這個字眼,但是並不會喜歡所謂的「竭盡所有勇氣」的表現。雖然說只是不擅長發揮原本就存在的東西而已,不過感覺起來就好像是在找藉口,不去誠實面對過去的自己。 一認真起來就會很厲害。只要有心就辦得到。基本上就像是這些話,感覺上就是在虛張聲勢一樣。也有藉著自我暗示來激發出超過實力的想法,可是個人來說還是討厭那樣的思考方式。 因此,要是想對這點提出反駁就請隨意。 我並沒有要就此討論的打算。 只是,因為會不會喜歡上自己完全是由自己決定的,所以想要在重要的局面中重視自我的理論。 因為,在決定這場勝負的時後,能努力的只有自己,不會有其他人來幫忙的不是嗎? 所以── 「怎麼樣呢?」 我現在正全力以赴的,鼓起內心的勇氣,進行這輩子最大的戰爭。 敵人是到至今為止膽小的我。過去甘於因為速度過慢以至於無法追上前方身影,而被孤獨留下之立場的自己。 那是非常難以應付的強敵,想要獲勝的難易度甚至不遜於 但是我不想輸,想要獲勝。再說,這個人就是從那裡回來的生還者之一。 「反正又要再去了對吧?既然這樣──」 終於伸出手緊握住的手,現在絕對不想放開。 「像、像你這樣的普通人,不可能有那麼剛好可以一直倖存下來的!所以說既然是這樣,那我就至少可憐你一下,讓你可以在最後留下美好的回憶啊。要好好感謝我啊!」 「…………」 「快、快說你很高興啦─!」 覺得非常害羞,好想逃離這裡,一邊心臟怦怦跳的一邊啪啪地搥打他的胸膛。雖然像這樣的碰觸是第一次,但他的胸膛超乎預想的魁梧,似乎讓我的腦袋變得一團混亂。  「Anna,我說妳……還以為妳這麼突然是要說些什麼……」
Lotos Reichhart。既不是大人物,也不是有錢人,更不是英雄的一個普通德國軍人。
「Anna,我說妳……還以為妳這麼突然是要說些什麼……」
Lotos Reichhart。既不是大人物,也不是有錢人,更不是英雄的一個普通德國軍人。反正不會有什麼出息,因為不得要領所以總是抽中下下籤。 老實說,以男人來說感覺起來就是一個沒前途的傢伙,但是即使如此,我無論如何就是喜歡這個人到無法自拔的地步。 「我再不回營區就不妙了。」 「你是笨蛋嗎?是 「Michael 不是那樣的人!」 「吵死了啦,我就是討厭那個傢伙!」 大聲喊著,然後回想著事情發展至今的經緯。雖然知道自己正在失控中,但是因為明白已經沒有後路了,所以就很自然的伸出了手。 為了不要忘記,為了強烈的感受那時所產生的小小勇氣。 現在的我正盡最大努力,想要讓這一剎那化作現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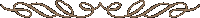 本在 所以,我就這樣什麼都沒說…… 對於在那一年之內完成了將校教育的課程,在新的一年就被派遣到東部戰線的他,我只能默默地目送著他的背影。 如果這是最後一次見面的話,該怎麼辦。這樣的想像讓我感到害怕……所以變成只剩下現在而已的心情,是非常痛苦的…… 我完全無能為力的,被留了下來。 「唷,安娜。好久不見」 但是很幸運的,他又回來了。他說的那個朋友似乎真的是個很厲害的人,擊破了好幾十輛的戰車,得到了總統頒贈的勳章。隨之而來的就是可以和他再度見面,心裡真的高興。 「你遠遠的被那朋友拋在後頭吶。已經不能跟他用對等的地位說話了吧?」 「囉嗦啦,別管我」 安心之後過於放鬆,我又說不出口想說的話了。 連要去碰觸那想緊緊握住的手都做不到…… 「不過嘛,實際上 Michael 真的是很強。只要跟他在一起戰鬥,就完全不覺得會輸啊!」 雖然他滿臉笑容的這麼說著,但是我是知道的。 英雄是沒有可以安息的片刻。更加激化的戰況,是不會允許休息的。 所以,只要有那個男人在,對他來說反而是種危險。普通的凡人若想與身披羽翼者一起飛翔的話,只會墜落地面、賠上性命。 「Lotos,到這邊來一下!」 然後,今日,1944年,6月25日──滿臉悠哉的伴隨著再度取得了戰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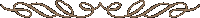  「
「「對自己的同伴感到自傲也不行嗎?」 「我在談的是你!」 將近是尖銳刺耳的聲音,但是總比哭聲要來的好多了吧。他那溫吞的應對,也許是因為想要安撫我說不定,不過就算是這樣我也不會受騙的。 戰爭是可以毫不留情的將生命奪走的東西,這事連我也能體到。 「去年,Eleonore 死掉了喔?那麼強的人最後也是那種下場,像你這種弱不禁風的人再怎麼耍帥看起來也只是很遜喔。所、所以,至少在現在……」 「什麼啦?」 「向、向我撒撒嬌也沒什麼關係的啦!」 明明是練習過好幾次的台詞,但是發出來的話卻是難聽到連抑揚頓挫都亂七八糟的。聲音在發抖。而且說的好快。語尾還聲音沙啞,真的是糟透了。 明明想要表現的是像個大姊姊,散發出成熟的魅力的說。 「不、不准笑─!」 再一次的啪啪地搥打他的胸膛。這下子根本就像個小孩子了。 嗚,全都是這附幼兒體形的錯啦。今年都要二十歲了,但是卻完全沒有成長。 連這樣一個沒出息的男人,都沒有辦法隨心所欲的誘惑他。 但是,事到如今已經沒有退路了。 「要撒嬌的話,還是更豐滿一些的胸部會比較好吧。」 「自以為是的在說什麼啊,你這種人這樣子就足夠了,應該說,就算是這樣對你來說也嫌太奢侈了。搞不懂自己的立場嗎?」 「什麼啦?」 「不、不不不過是個處男!」 「……………。」 「啊,咦,不是嗎?」 「……這個嘛。」 「喂──,你開什麼玩笑了啊啊啊!」 那是,等等,不管再怎麼說,就事情發展來看不是偏離的過頭了嗎。 吶,神明是鬼嗎? 「好痛,笨蛋,喂別扯啊!」 「何時、何地、你是跟什麼人!」 是那個嗎?在戰地搭上了某處的村姑嗎?這傢伙就像以前的傭兵一樣,炫耀今天可是大豐收啊之類的。 「不,不對,不是這樣。完全沒有那種肉食的氣息。」 「妳自己一個人在那理解什麼東西啦?」 「那、那,是那個嗎!」 隨軍軍妓?聽說只要有兩個以上的男人聚在一起,就會做出一起湊熱鬧的去那種地方的蠢事。 「可惡的 Michael~~~~」 「所以為什麼會冒出他的名字啦。何況──」 捉著我胡亂揮舞的雙手,背叛者仰望著我。然後,真的就只是因為這樣,只是跟他四目交會就靜了下來的我真的是已經沒救了。 「那妳又是怎麼樣啊?」 「我、我嗎?」 「啊啊,說說看吧。」 「就、就是啊,那個……」 那種事,根本就不用問吧。 「這、這個嘛,差不多隨便算算就有十幾二十個人呢。酒館的 Anna 小妹可是很受歡迎的……經常有人在出兵前拜託我,希望可以當做回憶跟他們來一次呢!」 「…………」 「那、那個眼神是什麼意思啦。不相信我嗎?我說的是真的喔?我跟 Beatrice 可是被稱做柏林的紅雨呢!」 「那傢伙不是完全沒有男人要追嗎?」 「我可是有很多男人想追的,很受男人歡迎的,每天都笑呵呵看著男人們為我爭風吃醋的!」 「既然這樣,那就用不著特地找我當對象吧」 「所以我說你啊~~~~」 偶爾會覺得這傢伙該不會是故意用這種態度對我的吧。 從以前就是,讓我懷疑是不是被討厭了而感到不安。 「我讓你覺得為難嗎?」 這種就好像是懇求般令人臉紅的話,這不是說出來了。 「不是那樣的,不過做這種事反而不吉利對吧?」 「那你是說你想要等這場戰爭結束以後就什麼什麼的那個嗎?相比之下那個感覺起來不就非常確實的有會完蛋的氣息了!」 「唔,的確,這麼說也對。」 「而且,你不是說過嗎,要活在現在。」 雖然已經是五年前的事了,但是在那個聖誕夜他確實是這麼說的。 在戰爭中,不知道有沒有明天,連何時會死都不知道。但是,正因為如此才更加的想要重視這一瞬間。就是這樣子,讓我們乾杯── 因為被說了要在現實中努力的活著,所以就算是我…… 為了不讓這個剎那從手中逃走,而在奮鬥著。 「你逃了是要怎麼辦啦!面對勝負就要好好的接受挑戰!」 「話是這麼說沒錯,不過男人可是 「你該不會是打算要說你硬不起來吧!」 感覺得到的回應似乎會是危險的台詞,我不經意大叫了起來。真要是這樣,不管再怎麼說,我也只能當場化成灰了啊。 這樣說起來,也不是沒有感覺到在臀部下面的反應似乎還挺遲鈍的。 「就、就交給我吧。輕而易舉的事情。我有豐富的經驗,不過是一兩個像你這樣沒用的男人,再怎麼樣都可以讓你們又大又硬!乖、乖乖的認命,就都交給大姊姊吧。這樣的話,我、我就帶你上天國去喔!」 「噗──」 「所以就叫你不要笑了─!」 「等、妳、別哭啊!」 「我才沒有哭!」 邊說邊甩著頭之下,眼淚向外飛了出去。然後我的頭髮,就在這個混蛋的臉頰上反覆的來回打著耳光。那是總覺得很丟臉,差不多該感到挫折的感覺。 「啊啊,真是的……」 ……結果,這就是極限了吧。我也沒有可以一擊 KO 掉他的鐵拳,已經不知道還能怎麼辦了。 就在放棄準備舉手投降的時後,不知道是哪裡的什麼人輕聲低語地說到。 「我只是想要 Lotos 的小孩而已。」 交雜在床舖被壓擠而發出的聲音中,說出了那種事。 「欸?」 「咦?」 是誰說的?是我? 「啊,咦?不是,那是什麼意思?」 「咦、咦……唔咦咦咦咦咦咦咦咦!」 等、等等等等等等一下── 「不、不不、不是、不是不是什麼都沒有啦啊啊啊!」 「妳說想要小孩子……」 「記憶給我消失吧啊啊啊啊!」 「──喀噗!笨蛋,別往人的心窩打啊!」 啊啊……啊啊,沒錯。要奪走記憶應該是打頭才對啦要打頭。 「啊,喂等等,不是這樣吧!」 伸向擺放在一旁的花瓶的手,被緊緊的握住了。 「冷靜點,不對請妳冷靜。先深呼吸吧,吶?」 「吸─,吐─」 「很好。那麼?」 「你還是去死吧啊啊啊啊!」 「為什麼妳變得比剛才更危險了啊啊啊啊!」 吵吵鬧鬧的糾纏在一起。 像這樣扭打在一起不知道經過了多久。我低頭看著一點也不讓我對他做出最後一擊的笨蛋,然後開口說道。 從害羞在到生氣的繞了一圈以後,感覺上就好像是進入了頓悟的境地一樣的心情。 「你認為這場戰爭會有勝算嗎?」 剛剛不小心說出了真正心話。雖然在說出來以前我也是沒有自覺,但是我發現到了那是最真實的願望。 我想要這傢伙的小孩。想要讓現在連繫到未來。 因為,那個時後大家一起發過誓的。希望可以總是向上看、向前走,然後一起乾杯的。 「我知道你很努力,也知道 Michael 真的很強。但是,Lotos……一定沒用的。這場戰爭會輸的啊!」 像我這樣區區一個村姑也足以理解,戰爭已帶著濃厚的敗色。 恐怕就在今年,不,一年內這座柏林就會被攻陷。 這種傳言到處都可以聽到,事實上士兵們早已疲累不堪了。 就算是虛張聲勢的說沒有問題,也沒有能力裝模作樣了。不具有那樣的包容力。 因為我的胸部很小。所以沒有能力可以硬著頭皮忍耐啊。 「所以,讓我看到前方的道路。因為現在是很重要的……所以想要讓你可以繼續的往前走。」 「那是 Riza 的……」 「嗯,我從她那現學現賣的。」 國家體制也好,或是家族也好,結果都是一樣的。沒有女人跟小孩就無法存續。 所以要孕育出生命,守護它,然後撫養它。就像是為未來開啟一道亮光。 她的這種想法,我現在有了相同的感受。 「不想也不願去想你會死掉。但是,Lotos,不就正因為如此嗎?如果說男人要挺身而出去戰鬥,那麼女人也該有要挺身而出的場所對吧?」 「……………」 「請給我那樣的地方吧。我厭倦被孤獨地留下了。」 不管是 Riza 還是 Eleonore 或是 Beatrice,或是這傢伙跟 Michael,還是 然而只有我,只有我什麼都沒有。對這樣的自己感到自卑沒有自信,就是一切的原因。 現在也終於明白,一直沒有緊緊的抓住這傢伙的勇氣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我想要勇氣。」 我想要有光。想要擁抱這個剎那。 「吶,給我吧。我想要 Lotos 的小孩。」 「我……」 「再說,也只有我了啦。會好事地屈就於你的人。」 「妳這傢伙……」 他一臉苦笑,我也露出了笑容。 嗯,這樣就行了。從我貧弱的胸中產生出來的勇氣,在這裡就是極限了。 不論是在今後,或是在更遙遠的地方,都會一邊培育他所給予我的東西一邊獲得勇氣。 因為勇氣不是硬擠出來的。是孕育、培養,被賦予的。 「那,我也有兩個條件。」 「是什麼?」 「第一,孩子……不,孫子也沒關係。總之就是讓他住去日本。」 閉著一隻眼睛做出稚氣的表情,Lotos 提出條件。那就像是平常的他,總是在開完笑般的語氣。 「雖然說要是我能去是最好,但是如果我不行了的話,希望妳能這麼做。我想要立刻達成是很困難的,但是拜託 Riza 與 Beatrice 的話,總會有辦法的。能用的人脈就盡量用。」 不知為何,直覺的就認為他所提出的這個請託,是絕對非達成不可的真摯心願。 「從那次聖誕節過後,我就一直想去日本,想的不得了。吶,拜託了啊,Anna。」 「…………」 「不行嗎?」 「不……我知道了。」 完全不知道理由,連何時能做到都不清楚,但就此立下約定。 因為既然你都說了是那麼地渴望能去日本,所以總有一種在這之後不論如何都會在該處在相逢的感覺。 「那麼另一個條件是?」 「啊啊。是說其實這才是最嚴重的問題啊。」 這次一下子就變成嚴肅的表情。不知道到底會是什麼事── 「我硬不起來啊。」 「…………」 「唉呀,真傷腦筋。該怎麼辦。妳可以模仿 Riza 的聲音嗎?她的聲音超性感的,如果閉上眼睛聽到的話我想就可以慾火焚身了。」 「………………」 「吶?」 「老……」 「老?」 那個誰,把 最後終於捉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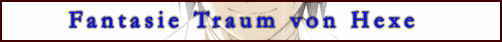 「──我當時這麼說過呢。把想像力膨脹到最大極限,確信 「這、這樣啊……」 「很不妙吧?」 我在打盹半夢半醒的,好像聽到身邊傳來了嘮嘮叨叨的在說什麼蠢事的交談聲。 「這麼說了之後啊。莉莎的臉頰就稍微的紅了起來喔。嗯嗯,不會錯的。騙不過我的眼睛。在當時,啊,現在也是,少女對那種事可是很敏感的呢。可不是白白的因為蠻橫的上司犧牲掉了難得的聖誕節,而在饑渴著愛情的喔。我很可憐對吧。」 「欸、欸欸,那還真是……當時 Kircheisen 女士不過十來歲吧?的確,雖然說是因為時代的牽連,還真是遺憾呢。」 「對,就是這樣。你說的真好。」 煩死了。煩死了。煩死了啦那邊的老太婆。都幾歲的人了就不要對年輕小伙子講過去那些丟臉的事啦。 「啊啊,但是,剛剛有個要扣分的地方。應該要叫我 Beatrice 才對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重來一次。」 「Be、Bea…trice。」 「是。有什麼事嗎,戒先生?」 ……………… 「呃、呃,那個,我去看一下妹妹的情況。」 「唉呀呀,那可不成。她現在正跟香純和 Erii 還有鏡花在一起,替玲愛挑選禮服呢。隨便闖進去是會被當成色狼的喔?還是說,其實你打算要去偷窺?我可是不允許花心的喔!」 「花、花心……?」 「啊啊,怎麼會這樣,多麼冷淡的男性啊。初次見面的時後不是這麼說過了嗎。從今以後,會永遠在身邊扶持我的。那難道不是在求婚嗎?」 「不是,那該說是業務上……」 「唉呀、唉呀、唉呀。該怎麼辦。戒先生居然想要拋棄我不管了,現在感覺心痛的好像胸口要被撕裂了。」 「什──,我絕不會把 Kircheisen 女士──」 「Beatrice。」 「把 Bea、trice……」 ……………………………… 「抱歉,戒兄。我要去外面抽根煙。」 「等、等等我啊,司狼──」 「唔呼、唔呼呼呼,這下子妨礙者就消失了呢。」 ……………………………………………… 「好了,差不多也到了該認命了的時後了喔。既然都到了這個地步,那麼乾脆我們也搭便車――」 ………………………………………………………………………………………………………………………………………………… …………………………………………………………………………………………………………………………………………… 「在這裡對永遠的愛──」 不,稍微等一下吧。 「別給我色慾薰心了!這個妖怪老太婆啊啊啊!」 猛力開門發出的啪噠聲,讓我也終於完全清醒了。也許是年紀大了的影響吧,耀眼的光線讓視線無法立即恢復,不過總之因為他的現身,保住了純樸青年的貞操。 「聽司狼說了就過來看看,妳這性騷擾老太婆還真是學不乖啊。戒先生也是,反正只不過是在逗著你玩的,不用跟她那麼認真也無所謂啦。」 「啊,嗯……不,抱歉。」 「等等,你還真是老樣子不懂得對長輩的說話方式啊。對我也就算了,不是跟是說過跟戒先生講話要更有敬意嗎?」 「那種事等妳學會什麼是矜持以後再說啦。算我拜託妳了。」 「啊啊,真是個強詞奪理的孩子。就算只是形式上的,明明在今天終於就要變成獨當一面的大人了。這樣子的話是沒有辦法讓玲愛得到幸福的喔?」 「那還真是不好意思啊。很遺憾的,這個部份跟某人可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啊。」 「呵呵、呵呵呵呵……」 「哈哈、哈哈哈哈……」 兩人發出了就彷彿是在威嚇彼此的笑聲。 這個部份該說是同步化了還是什麼好呢。養育重於生育什麼的,看來是真理。 老實說總覺得是該起來了,但這情況挺難纏的。再試著睡一下吧。 就在這麼想的時後。 「啊,Anna 女士好像醒來了。」 「咦?」 「唉呀。」 ……喂喂。 一旦像這樣子被注意到,不就是連想假睡都沒辦法了。 無可奈何的只好放棄,揉著惺忪的眼睛嘟嘟嚷嚷的起來了。 「戒~,你是個好孩子,但是偶爾也不會看氣氛呢。」 「咦……啊,是這樣嗎。不好意思。」 「好了好了。沒關係啦,開玩笑的。其實剛剛就已經醒了。因為某人在講蠢話呢,Beatrice。」 「唉呀真過份。要怪到我頭上嗎,Anna。」 「不就是妳的錯嗎。」 不論是在打盹時,所做了的令人懷念的夢。還是在清醒後的現實裡,跟夢境相連的事物。 一切,都是因為有妳這個朋友在的關係。 讓我可以在這裡,感受那個人授予我的未來。 「呃,那這邊想要再確認一次。」 相同的聲音。相同的面貌。雖然跟 跟 看起來兩人就像在血緣關係之上的不同次元,重疊在一起似的,這是我多心了嗎? 「玲愛希望在婚禮紅地毯上可以拜託是曾祖母的兩個友人其中之一。真的要這樣的話,就要讓那個人跟在其中一邊。」 「你也要一起走吧?」 「……這個嘛,雖然不知道是為什麼,不過就是這樣。戒先生也跟她說一下啦,男人在走婚禮紅地毯,完全就是搞錯了嘛。」 「是男人的話就別在現在還囉囉囉嗦嗦的了。」 「等等,妳以為是因為誰的關係才變成需要拜託 Anna 女士這種麻煩事的啊。就因為妳任性的說要一起走的話就要跟玲愛在一起。」 「因為我還沒有要放棄結婚喔。所以想要在近距離的為今後的打算好好的觀察一下。」 「就是這樣。真的要小心啊,戒先生。」 「啊……,嗯,哈哈哈哈……」 「真的是很抱歉,Anna 女士。」 「不會,我也很高興喔。」 是的。原本在他的身邊,站的應該是養育他長大的 Beatrice。就算是為了要遵守約定,離這個孩子而去的我是沒有資格的。 所以,當然也沒有告訴他我是什麼人。 知道真相的,現在只有 Beatrice 一人而已。對於在斟酌之後,為我安排了這場演出的她,有著無以復加的感謝…… 「謝謝妳,Beatrice。」 「不會不會,別客氣。」 這個心思細膩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沒有對他說出真相的另一個理由…… 「我現在非常幸福。這一定是場夢。」 Lotos……,在我眼中,你和這孩子幾乎是完全重疊地。 會如此相似自然是想當然爾,但我更超脫了這常識的窠臼,強烈的認為。 我還活著。 向前走去,在 無法向任何人訴說的真心話。 雖然對不起玲愛,但這不過是無害的妄想,應該無傷大雅吧? 我現在,讓心靈回到少女──   「那麼,動身吧,Anna 女士。」
「那麼,動身吧,Anna 女士。」握住伸向自己的手,低呟著。 從大家那裡漸漸得來,自己當時不足的勇氣。 「我愛你,Lotos!」 獻給他的魂魄,那長達七十年的思念…… 正田崇 『Lotos X Rusalka Original short story』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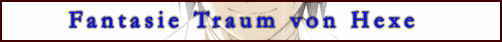 |
【wiederkehren】 (C) Light dies ira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2006~2010
当ページはlightより画像素材等の使用許可を得ています。
本頁所使用之畫像素材之類,既經light同意。切勿無斷轉載。